根據長年投入身心障礙運動平權議題,來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姜義村教授(特殊教育學系暨復健諮商高齡福祉研究所)的研究團隊指出,台灣社會中存在著一群經常被忽略的特殊需求族群,他們並不在主流的運動政策的施政焦點中,也不在主流媒體的鏡頭裡,但他們同樣是國家運動權相關法令的保障對象,也不斷努力追尋一種屬於自己的自由。這些研究資料提醒我們,若要談「運動平權」,就必須重新審視「誰的身體被允許運動,誰被排除於外」。
讓我們先從兩個數字及一個事實說起。
從近五百萬的熱鬧開始:那些「被看不見的徒步行走」
每年春天,台灣的道路都會被一種集體的徒步行走活動所佔據。白沙屯媽祖、大甲媽祖、北港朝天宮,一場場徒步進香與繞境活動,不僅是文化信仰的壯舉,也是一場全民健走的身體實踐。

根據主辦單位與遠見雜誌統計,2025年白沙屯媽祖進香吸引超過70 萬人沿途參與、33 萬人報名,而大甲媽祖遶境更在清明連假的情況下,創下了400萬人次參與的新高紀錄。在其中,45歲以上的人數約占一半,而60歲以上的族群則超過5萬人(10%)。他們每天步行20公里以上,頂著烈日與炎熱與痛苦同行。然而,這些參與的群眾並不被視為「運動者」。在教育部與運動部的主流價值分類中,進香與繞境活動可能被視為「文化活動」,而非刻板印象中有競技價值的「運動」。然而,我們必須承認,「信仰型運動文化」的定義中,臺灣媽祖活動的徒步進香遶境的確就是運動,而這群高齡者與身心障礙者的參與運動權不應該是運動部「適應運動司」應該忽略的對象。

超過六萬人的極端:被禁錮的身體
再把鏡頭拉向社會的另一端-那些在高牆之內的群體。
截至2025年8月,法務部矯正署統計,臺灣矯正機關的實際收容人數為61,949人。若以全人口中約5%為身心障礙者的比例推估,代表約為3,100人左右的矯正對象同時具有身心功能受限的情況,並且人數可能更高,其中以心智功能受限為主,如智能障礙、自閉、過動或失智等。如此高壓的監禁環境下,同時具有躁鬱、憂鬱或思覺失調等精神疾患需求者或許也是大量需要關注的對象,因為其中領有上述的身心障礙手冊者應只是少數。其中另外需要令人關心的是臺灣有四所矯正學校,根據CRPD國家審查建議,這群未成年的青少年不少仍處於國民教育階段,也有比一般學校高出數倍的特殊教育學生。


透過適應體育深耕計畫的支持,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借用相關器材設備給矯正學校舉辦虛擬實境單車騎乘競賽,引發參與學生強烈動機。
據教育部體育署(2025)函調4所矯正學校持有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人數估計約佔總人數的10%,其中又以學習障礙與情緒行為障礙為多數約8%,因此,應該確保他們的體育課受教權,然而,由於主管機關是法務部矯正署,如今運動部成立,在適應運動司的業務規劃時,是否忽略了這群關鍵少數?
這個群體其實有強烈的運動需求,但卻被制度剝奪了實質體育課程的權利,多數矯正學校與監獄仍多數以「紀律服從」或「管理控制」取代實質體育課或運動時間應授的教學內容,並且一般而言運動場地相當受限、專業運動或體育師資缺乏、運動器材設備也相當簡陋。然而,對這些學生與受刑人而言,「運動」不只是流汗與伸展,更是重新學習自己存在意義的一種方式,一種在被矯正的世界裡,重拾秩序與自信的教化契機。
兩個極端的並置:被遺忘的運動主體
一個是自願投入行走,卻被運動體系忽略的關鍵多數;一個是被拘禁約束,而被剝奪享受運動的沉默少數。
姜義村教授指出:「前者人數眾多,卻鮮少被視為『運動參與者』。然而,實際上投入進香、遶境的中老年、亞健康人士,他們面臨極大的體能挑戰,健康狀態也尤其讓人關注。」姜教授接續說明:「而後者,矯正學校中的特殊需求學生則偏屬於『人少但需求強烈』的關鍵少數族群,這些人多有行為偏差、情緒障礙或身心障礙背景,長期被社會與教育體制邊緣化,更是『社會安全網』建置中經常被忽略的漏洞。」

兩個族群都是向陽處的陰影,我們未能知悉,沉默卻又亟需資源的人們。這兩個族群都呈現相同的事實與現象,構成了一種被制度排除的不平等:「一個被信仰包容卻被政策忽略;一個被國家拘束卻被社會遺忘。」在這之間,藏著的是我國運動文化長久以來的盲點-誰有「被允許運動」的資格?
關鍵多數與沉默少數
在國家體育政策的架構中,「運動」長期與「榮耀」綁在一起。根據教育部體育署近年預算資料(教育部體育署,2024),競技運動相關經費長期占整體體育預算的大宗,其經費常是「全民運動」項目的三倍以上。以「運動壯大臺灣」為願景,提升臺灣在國際體壇能見度的運動部,不證自明,其施政方針會著重於競技運動與選手、教練栽培上,這當然是台灣體育界一等一的大好事。然而,其憂心之處在於,跳脫教育部『體育』策劃下,一來是否會導致資源過度集中於同一族群身上?二來,潛藏於陽光下的『關鍵多數』、『沉默少數』是否能得到妥善的安置與照顧?這樣子的政策施為也將使得非競技族群,包含高齡者、身心障礙者與社會邊緣群體,將在政府制度設計中長期處於資源邊陲。運動,也因此被定義為「競賽與奪牌」的代名詞,而非「基本人權」。

同時,教育部體育署《113年運動現況調查》報告中指出,民眾參與運動的主要障礙包括運動場所距離過遠、設施不足與無障礙環境缺乏等,顯示運動不平等早已不是個人意願問題,而是結構性問題。台灣適應身體活動學會前理事長也是臺師大特殊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徐一騰分享道:
「在徒步進香、遶境的路線上,無障礙廁所數量有限、品質參差不齊。輪椅使用者難以找到適合的通行動線或充電點。年長者行動需要適時休息,水分、電解質補給,或是住宿較難以找到相對合適的空間。」
這些問題,反映的不是信仰活動本身的缺陷,而是休閒運動之於宗教活動,缺乏體育運動觀點的介入。姜教授指出:「當成千上萬的人在行走、移動,這本身就是一種運動。…運動部應該認知這是一種運動文化,亦有平權的責任。」但因為當運動與信仰結合時,容易被歸類為文化信仰活動,而缺乏運動專業的參與,「我們跑馬或玩鐵人三項的人都知道要比賽配速是關鍵、平常練習都要用運動手錶監控、更有運動強度、訓練週期等運動專業觀點,而長達十多天的徒步進香遶境當然更需要,更何況是高齡者和身心障礙族群,這部份運動部若是忽略或不重視,除了失去全民運動這個區塊的「超級業績」,更像是眼睜睜看著一大群國民在萬丈深淵中走鋼索,根本是瀆職!」姜教授開玩笑地描述著。

信仰型運動文化:當徒步進香繞境已成為全民運動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13年運動現況調查(2024),國內民眾最常從事的運動為戶外休閒運動(78.8%),並且集中於對散步/走路/健走之喜愛,蟬聯統計第一名(57.4%);然而,超過七成運動民眾是「為了健康」而運動,凸顯了大多人的運動動機是來自於外在壓力而非享受運動,但運動從來就並非只是為了健康的手段,健康或許是附加而來的價值,真正讓人動起來的,往往是運動的意涵。
徐一騰說道:「在每年一年一度的白沙屯媽祖與大甲媽祖的徒步進香與繞境活動中,每年有數十萬人行走破百公里,這場長距離的步行活動已然超越傳統的信仰儀式,成為一種結合信仰的新型態運動文化。有民眾說:『為了能跟著媽祖婆走,我每天都要運動練體力。』有人為了到時參加徒步進香不掉隊,也會提前就開始進行訓練,甚至有的輪椅朋友為了參與,還特地揪團一起督促彼此進行鍛鍊。」他們不是為了健康,而是為了能與其他人一樣,享受能走能動,參與其中的感受。

心理學家Deci與Ryan(2000)指出,人類最持久的行動來自「內在動機」,不是外在獎勵,而是來自自我決定與社群連結。信仰型運動文化正是如此,沒有獎牌,無須成績,卻有強烈的牽絆與動機。信仰給了人們前進的理由,社群讓人不願中途離隊,日常的運動成為一年一度參與另一種賽事的備戰準備。
這種戶外運動是台灣最在地,也最被低估的「全民運動」,它門檻低、可持續,並且具有高度黏著性。當我們談到「運動平權」時,不該只看競技場上的速度與榮耀,那些在夕陽下一步步前行的另一種馬拉松選手,早已以另一種方式實踐了全民運動的精神,不是為了得獎,而是為了感受信仰與運動結合的自由。
矯正學校中的沉默少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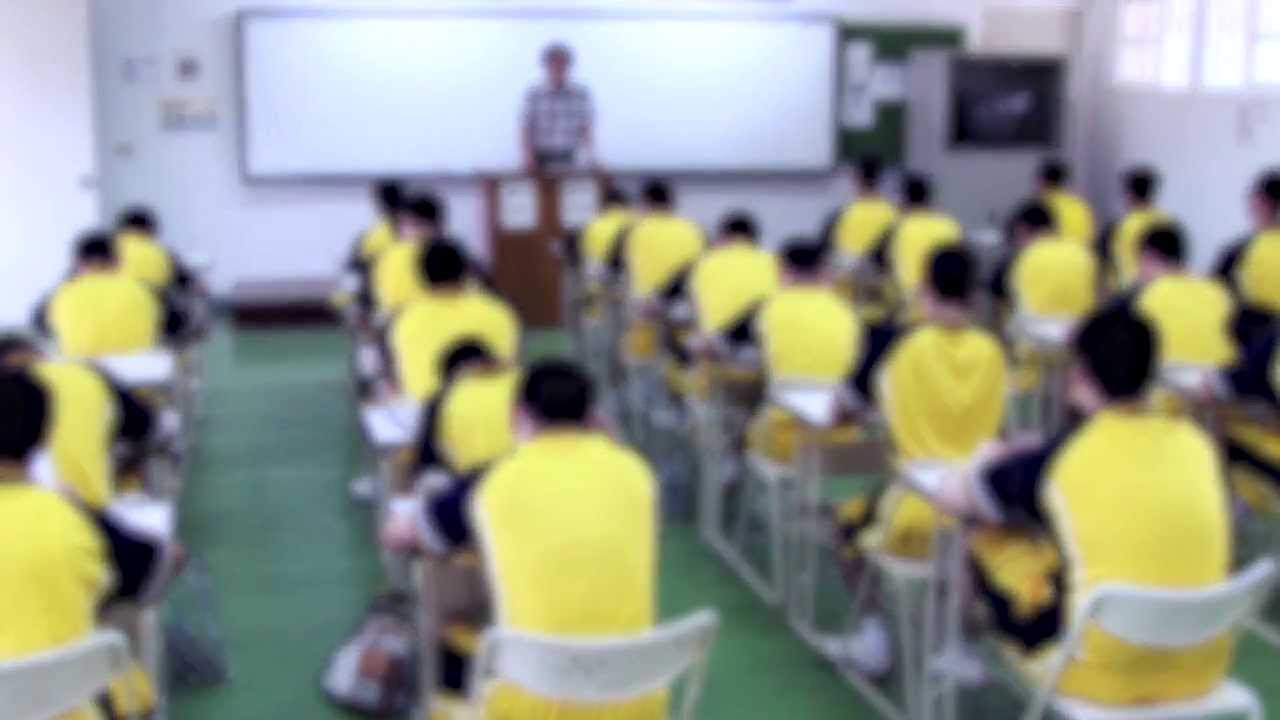
此外,相對於宗教之於運動、容易被忽略的「關鍵多數」,處於矯正學校中的身心障礙學生,則屬於「人少但需求強烈」的沉默少數。許多人或有行為偏差、身心障礙背景,使得被社會與教育體制邊緣化。他們沒有引以為樂的運動日常,同樣的,或許也沒有相同的資源與規模設施。台灣適應身體活動學會前秘書長也是臺師大特殊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葉翰霖表示:
「他們是最需要運動的一群人,運動能讓他們重新建立秩序與自信。」他表示在矯正學校的教學經驗中發現有不少受感化教育的學生曾經參與過運動代表隊、讀過體育班,但因為許多社會環境或成長不利因素,最終走入司法系統。葉翰霖強調:「我們最需要重視的,不是如何懲戒,而是如何修復-修復他們與自我的關係、與他人的信任、與社會的連結。若要讓他們能重新建立親社會行為與正向價值觀,運動和體育課會是矯正學校裡最有力的教育工具。我們呼籲運動部適應運動司應該重視這些關鍵的少數,因為這群孩子長大後就在你我的身邊生活著,我們當然希望他們能感受到社會的溫暖、愛上這社會,而運動正是最能修復人心的力量!」

然而,在過去的體育署架構中,這類場域往往不在關注範圍內,學校也缺乏資源與師資推動「適應體育」。當運動部成立之後,新的挑戰是如何整合跨部會資源—例如與矯正署、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合作,建立矯正體系內的適應體育課程。這不只是體育教育,而是社會復歸與人權平權的重要一環。
從榮耀到共榮的運動平權:運動不只是金牌
若「運動平權」要成為真實的社會目標,我們必須重建想像,「獎牌等於國力?」這是個大哉問。長久以來,政策編列大量資源在競技運動上,然而,休閒運動或是非競技專業的運動大眾,卻難以享有同等的福利與資源,尤其針對適應體育、特殊需求者更甚。「針對適應運動的競技運動,資源挹注與使用者往往是同一批人。有關身心障礙者的運動預算又將相當高的比例投放在數量相當少的菁英選手培訓系統上,不論是用來出國比賽、培訓經費或獎勵獎金,而手中握有選票的多數身心障礙者都會想著『運動與我又有何干』?如果不重視大多數的身心障礙者的運動權益,相信不論是政府單位或是民意代表都必將失去民心,而被民眾用選票淘汰!」姜義村教授強調說明。

從榮耀到共榮的運動文化平權,不能再將奪牌做為運動的代名詞
推廣全民運動的重點在於:
- 重新定義「運動主體」,運動不只是速度與競技,而是「基本人權」,政府應在體育運動政策中納入非競技、信仰型運動等多元之運動文化類型。
- 在矯正教育體系中,將「適應體育」納入教育核心,體育運動不該只是獎懲手段,而是讓人重新學習與修復的途徑。
如果運動部能從這裡出發,這將不僅是一場行政分工的重整,更是「運動文化的再定義」,我們認為,真正的 #運動平權 不應被侷限在競技場,也不該是特定族群的專利。讓更多國民都能在運動中找到歸屬感,那麼「運動強國」將不再只意味著金牌數量與掌聲,而是做為一種「基本人權」的存在,那這時我們才能大聲的說,我們真正的踏入「全民運動」的時代了!














